李澤厚: 為什么巫術才是中國獨特傳統的核心根源?
我今天講的題目是《由巫到禮》,這是個很難講的題目,因為牽涉到上古史,材料不夠,我自己研究得很不夠,學術界好像也研究得不夠。這是個非常重要,卻被忽略掉的問題:所以的確值得講一講。特別是這個問題與中國整個文化、中國整個哲學的特征,很有關系,這就成了一個大問題。
中國文化、哲學有什么特征呢?當然有很多了。例如,比較其他文化來說,在中國文化里,人的地位就很高。天地人三才,人可以跟天地并列,可以“參天地、贊化育”。人能夠參與天的運作。我記得20世紀80年代一個反傳統的學者說,中國文化的最大的缺點、最大的問題,就是人的地位太高了,所以必須把基督教引進來,人必須在上帝面前悔罪,認識自己有原罪,不要把自己的地位估計得那么高。《圣經》里沒說人能夠參與上帝的工作,上帝說要有光就有光嘛,人能起什么作用呢?
盡管我不同意這位學者的看法,但我認為他抓住了這一個要害。中國《詩經》里面有罵天、埋怨天的話,說天不可相信。包括今天老百姓常說的“老天瞎了眼”,直接就罵天,也沒感到什么特別。中國沒有創造主這個概念,沒有上帝造人的觀念,認為人就是父母生的,所以罵罵天也沒有什么,但不能罵父母。人的地位這么高,這一現象,很多學者都指出過,問題是它怎么來的?
還有,中國為什么到現在,歷史這么悠久,始終沒有形成那種絕對的、全知全能、主宰一切、遠遠超乎一般世俗生活經驗之上的一種神,像猶太教的神,基督教的神,伊斯蘭教的神。中國老百姓相信的關公、媽祖、觀音菩薩,都是跟世俗生活聯系在一起的,而且他們本來就是人,由人而神,人神同質。關公本來是關云長,是個人,媽祖也是,對不對?這是怎么回事?中國始終沒有形成那種開天辟地的絕對神、至上神。猶太教在宋代就傳入中國了,現在開封附近還能找到猶太人后裔,但猶太教沒有了。
基督教大家都知道,明代也傳到中國,但至今在知識分子里面形成不了普遍信仰。為什么?中國知識分子到現在為止,說他是信神呢,有時候又不信,說他不信神呢,有時候又信。還是孔老夫子講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祭的時候就相信是有這個神明在的,但不祭的時候也就不想了,不像伊斯蘭教每日五拜,天主教每飯謝恩,基督教七日去教堂聽經祈禱,等等。所以墨子早就罵儒家是“以天為不明,以鬼為不神”。
講中國是“一個世界”,為什么呢?因為與對鬼神的態度一樣,中國人的另一個世界也是相當模糊的、籠統的、不明確的。對中國人來說,另一個世界似乎并不比這個世界更重要、更真實,相反,另一個世界倒似乎是這個世界的延伸和模仿。人死了,古代要埋明器,現在就燒紙房子、紙家具,讓死人繼續享受這個世界的生活。另一個世界跟這個世界并沒有多少差別,另一個世界實際是為這個世界的現實生活服務的。中國人很講實用,很講功利,到廟里去燒香的,求福、求子,保平安、祛疾病,都是這個世界的要求,為了一些非常世俗的目的,很難說是真的為了拯救靈魂、洗清罪惡,等等。為什么?這些文化上面的特征,是怎么來的?安樂哲(Roger T. Ames)《孫子兵法》一書也指出,不同于西方傳統的兩個世界,中國是一個世界,但沒說這是怎么來的。中國人必讀的六本書
拿哲學來說,西方從希臘哲學到海德格爾,Being是個很大的問題,這個詞在海德格爾那里是最重要的了,他最有名的著作是《存在與時間》(Being and Time),但是到現在為止,中文還不能很好地翻譯Being這個詞。有人翻譯成“存在”,有人說應該翻譯成“是”,學術界始終有爭議。為什么?對中國哲學來說,這個問題好像不是特別重要,不是什么嚴重的問題。也就是說,中國哲學并不追求某種永恒不變、最高本源的“真實”世界的“存在”(Being)。相反,中國人是講究Becoming,講究生生不已,《易經》講“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認為這個變動不居的現實世界就是真實的、重要的、本源的,所以講change,不講什么Being。
中國哲學還有一個特點,在柏拉圖的對話里面,“美”不是一個美的姑娘,也不是一個美的盤子,它是美本身。What is beauty,什么“是”什么,中國人好像講得比較少,而總是講How to,How to do,干什么,怎么做。就像孔夫子在《論語》里面講“仁”講得很多,講了一百多次,但是仁是什么,始終沒有給出一個定義,總是這樣做算仁,那樣做算仁。重要的是怎么樣去做,這也就是宋明理學講得很多的“工夫即本體”,如此等等。
所有這些特點,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來的?在我看,就跟中國這個“巫”的傳統大有關系。但為什么這么有關系,今天卻被忽視掉了呢?包括學術界、學者們,都沒有重視這個問題。我想原因之一,是一般提到巫,就想到民間的巫婆。witch,中世紀的西方也有嘛,中國講是迷信嘛,那當然是很次要的了,所以不重視。在中國古代的記載里有巫祝卜史,也都不是很大的官,巫也就慢慢進入小傳統、民間,后來與道教合流,變得不重要了。在貴州有一種儺文化,戴著面具,跳各種各樣的舞蹈,現在都還有。這個現象在春秋,在孔子時代就有了。《論語》里有這么一句話,“鄉人儺,朝服而立于阼階”,鄉人跳儺的時候,孔子穿著上朝的衣服,站在東面的臺階上。孔子為什么穿著上朝的衣服站在大門外面呢?是表示尊敬,表示對巫術舞蹈的敬意。孔子為什么要對它表示敬意呢?因為它來源久遠,而且曾經地位非常之高,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它本是大傳統的重要核心。

我在1998年出版的《論語今讀》(3·24)里說:“與當時人們一樣,孔子大概仍是相信上帝鬼神的,只是采取‘存而不論’的態度,即不用理性(理知、理解)去解說神的存在,而是將某種理解例如對宇宙的存在及其規律性(‘四時行焉’等)的領悟沉入情感中,造成某種心理的信仰情態。”儺本是通鬼神的巫術儀式,雖然已淪為小傳統,孔子因為相信鬼神、上帝,即使有那種理性的情感信仰,又仍然穿著上朝的嚴肅服裝對這種本占據核心地位的久遠傳統表示敬意。
為什么說巫本是占據大傳統的核心地位呢?從甲骨文可見,巫與帝常常聯系在一起,帝巫。巫在當時,不是我們現在講的巫婆,當時最有權勢的人才是巫。考古學家,從陳夢家到不久前去世的張光直教授,他們的研究結果都表明王是首巫,最重要的巫,最大的巫。中國傳說中的古代圣王,例如儒家一直講得很多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根據很多學者的研究,他們都是大巫。《論語》里面講“堯則天”,中國古代的天文學是很發達的,而古代的天文與巫術、與當時的信仰是聯系在一起的。《論語》里講舜無為而治,面朝南而不動,他在做什么呢,有學者說他在施法術。
還有夏禹,大禹王治水,跟禹有關的有一種禹步,道藏里有,這是巫術的一種步伐,禹也是大巫。張光直考證禹的兒子啟,中國第一個真正世襲的首領——夏啟,《山海經》里說他舞《九代》,跳一種舞,這也是一種巫術。還有湯,商代的第一個皇帝——商湯,他的禱告是很有名的,當時天大旱,不下雨,商湯就把自己的頭發割掉,發誓假如再不下雨,他就死掉,把自己獻給神明。這是很著名的事情,果然下了大雨。巫師求雨在古代文獻中很多,《周禮》里就講率巫跳舞,率領群巫跳舞,做什么呢,求雨。因為下雨對農耕民族非常重要,天不下雨,農作物就活不了。這是非同小可的事,維系著整個群體能不能存活的問題。巫能溝通天人,請天下雨。
文王,有人考證也是巫。周公替武王治病,也是實行巫術,這在《尚書》里有記載。周公的兒子也是巫,也有明確記載。所以巫的地位在當時非常之高,是大傳統中很重要的角色,巫代表傳達、發布和執行神的旨意,本身也就是神,遠遠不是民間小傳統的那種巫婆神漢。
因此,我這里講的巫,不是講這個字,不是講巫祝卜史這種不重要的官,而是講這種非常重要的現象。這種現象可以一直追溯到舊石器時代。大家知道,19世紀在法國、西班牙發現了原始洞穴里面的壁畫,有牛啊,被射中啊,或者是畫在很黑的地方,要打著火把才看得清楚。這當然不是為了欣賞,像今天把壁畫當作藝術,當時就是用作巫術活動、巫術儀式,活動結束,最后留下的一些痕跡,這種活動在當時是非常神圣、非常重要的,幾萬年了。巫從那時開始,就是非常重要的現象。
這個現象對這個群體,或者對人來說,起一個什么樣的作用呢?這個作用很不簡單。通過這種活動、儀式,通過跳舞,把群體、把人組織起來。甲骨文里的巫字,與跳舞的舞字,就是一個字。巫就是舞,舞就是巫。跳舞不是一般的舞,不是為了文藝娛樂,而是具有很重大很神圣的、卻又是對現實生活起著重要作用的意義,為了求雨、為了狩獵、為了豐收、為了打仗。我這里有一幅著名的仰韶時期的馬家窯彩陶盆圖,距今4500到5000年以前,紋飾的圖樣就是舞,群舞,不是一個人,而是大家手牽著手都在跳。起什么作用呢?就是在群體里面,起著團結、鞏固、組織的作用。開始也許是亂跳,但后來很有講究,怎么個跳法,如何動作,左右手怎么協調,前后進退,面部表情如何,用什么服飾,我們現在看非洲和太平洋群島的原始部族,還穿戴著各種各樣奇怪的面具、服飾在跳舞。
通過這些活動使人的群體關系鞏固起來,互相的分工也很清楚,誰跳什么,步驟如何,都有很嚴格的規定。在人的主觀方面,則帶有很大的激情、情緒、情感,所以跳舞可以跳得很迷狂。但里面又有理性的東西,有想象,有理解,有某種認識,有的時候是復現打獵的那種情景。那些技術和記憶,都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種動物所沒有的人的心理形式即情理結構,在原始巫術活動中,培養發展出飽含理智因素(認識、理解、想象)的情感,這一點非常重要,它構成后世講求合情合理、情理交融的文化心理結構。總之,巫術舞蹈是最早的人類獨有的精神文化活動。它在遠古的時候,是維系著整個群體生存、生活的一種精神文化活動,是在打獵、采集這些生產活動之外的精神活動。最初這種跳舞、儀式可能是人人參與,如馬家窯那個彩陶盆所表現的(“家為巫史”),到后來就變成只能由王、君率領少數巫師來舉行,也就是規范化、專職化了(“絕地天通”)。
這樣的活動有什么特點呢?很多人類學家,比如泰勒(Edward Tylor),弗雷澤(James Frazer),包括韋伯(Max Weber),都講到宗教與巫術有很大的不同,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巫術是強迫對象來為人服務。中國稱之為呼風喚雨,通過人的活動,使各種東西為人所支配,而不是單方面的求拜。比如通過儀式,把箭射到畫的牛身上,也許第二天就能獵到野牛了。這是通過人的活動去支配自然界。我記得1949年之前,大旱的時候還有求雨的儀式,鄉民們把龍抬出來,叫作“曬龍王”。龍王主管降雨,旱熱得不行,也把龍王抬出來曬曬,強迫龍王必須下雨:表面是求雨,實際上是通過人的某種活動(巫術)強迫“龍王”“天”下雨。
上面提到的那些文化人類學都強調巫術與宗教的這個重大區別,即在巫術中,人的活動的能動性非常突出、非常重要,巫術就是通過人的活動來產生某些所企望、所要求的結果,而并不是人被動地跪在那里向神、向天、向上帝祈禱。與此相聯系的一點是,巫術里有神,但這個神是在活動中間、過程中間出現,跳著跳著就降神了。包括現在巫婆作法,也是念著念著好像神明就來了。神明是在過程中間出現,而不是一個什么固定的、很明晰的神明坐在那里等著人去求,神是在過程中來的。從而,什么神明來倒不重要,往往是很模糊的、多元的、不確定的,跳著跳著感覺就來了。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說,敬神的儀式比敬神本身還重要(見《古代中國思想的世界》),芬格萊特(Herbert Fingarette)說,孔子的中心思想是禮不是仁,十分強調日常禮儀的神圣性,他的書名便是《孔子:即凡而圣》。巫、禮的神圣性都是在過程中、在活動中出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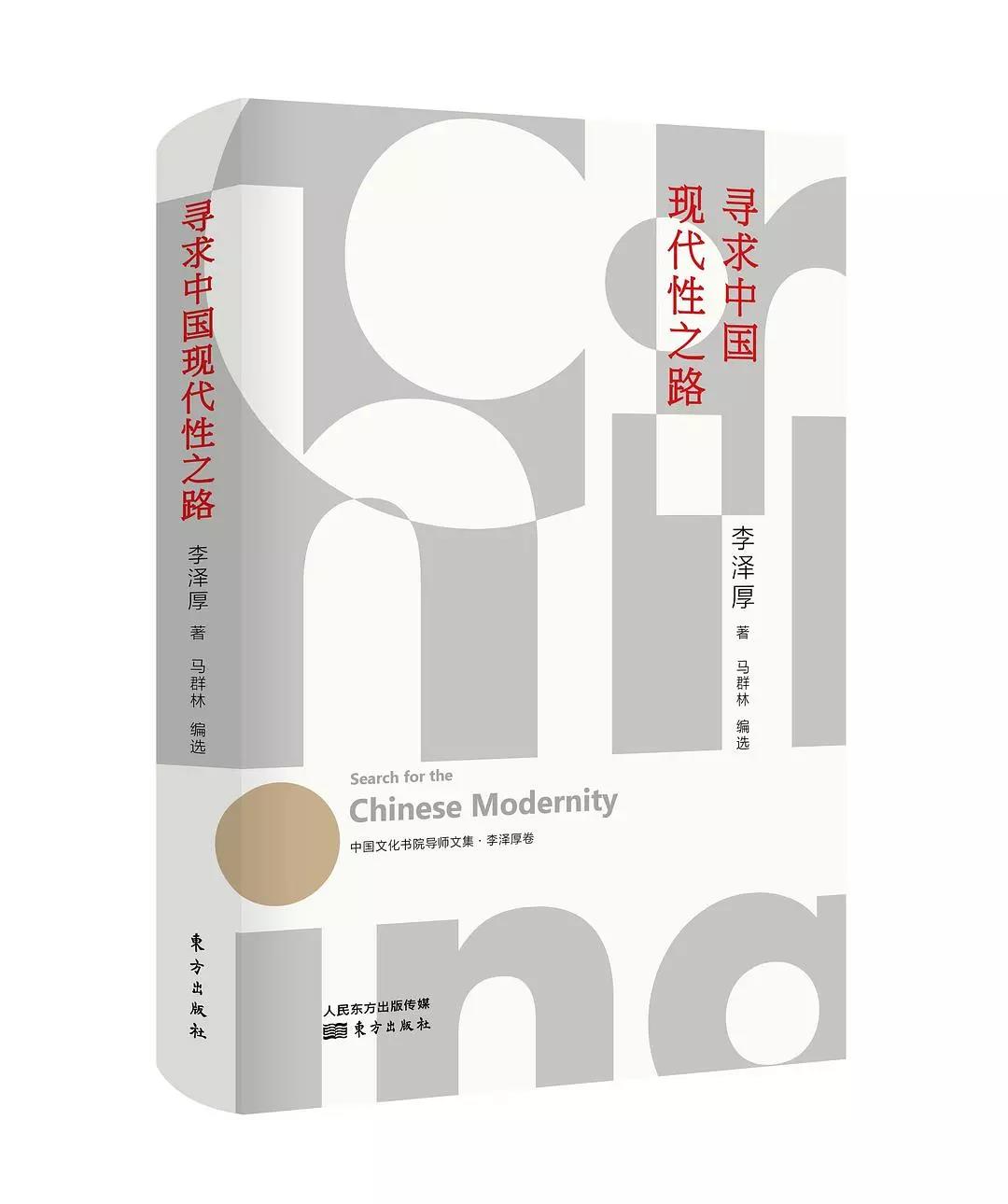
巫術活動這種現象,所有民族都有,西方有,非洲、南美洲也有。但是只有中國很早就把它充分理性化地發展了。在西方,巫術里有關認識世界的方面,技術的方面,包括那些高難的動作,變成了技藝和科學。中國學者李零講的方技也如此。而情感性的就發展為宗教,用宗教替代了巫術,后來在大傳統和精英文化里就沒有巫術存在了,小傳統里的巫婆也被基督教所嚴禁,大家都知道中世紀有大規模燒女巫的嚴重迫害。而在中國,我以為,巫在大小傳統里都保留下來了,小傳統便是今天還有的巫婆神漢,大傳統就是通過祭祀祖先的儀式慢慢變成精英文化的“禮儀”。中國人必讀的六本書
上述那些巫術基本特征,不但沒有被排除,而且經由轉化性的創造,被保留在禮制中,成了“禮教”。禮教成了中國大傳統中的“宗教”,正因為它,中國人(漢族)就沒有產生,也沒有普遍接受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為什么呢?因為神就在“禮儀”當中,嚴格履行禮儀就是敬拜神明,因此也就不需要別的神明主宰了。
何炳棣教授說的中國文明的兩個特征,我是很贊成的,一個是中國的氏族血緣延續得非常長久、鞏固,中國新石器時期非常漫長,生產工具很落后,鐵器到很晚才使用,但定居時間很早,農業開始得很早,因此協作性很強,工具不進步就得靠互相協作。因此群體之間的人的關系從開始就非常注意,怎樣協調,把個體之間的相互關系搞好,使之有助于群體生產。于是,以血緣紐帶為軸心所形成的人與人的“倫常”關系,便以“名”的稱號固定為等級秩序(即后來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成了社會主要的組織形態和生活秩序而十分重要。還有一個與此緊相聯系的特征,何炳棣指出便是祖先崇拜,很多民族也有祖先崇拜,但中國特別發達,一直到現在都是如此。很多人考證殷商的“上帝”就是祖先神,盡管到了周代用“天”代表上帝,但“天”反而顯得很模糊。“天”這個字,到現在為止仍然有雙重含義,一個是自然的天,一個是有賞懲權力的天。
中國人喊“天哪”,好像就是有神明在那里,但另一方面就是蒼蒼者天,自然的天。所以“天”并不是很明確,不是基督教上帝那種發號施令的人格神,中國的“天”沒有那么清楚。但是祖先神卻是很清楚的,祖先是什么,生時為人,死了成神,神本來就是人嘛。考古學家的地下發掘,發現中國新石器時期寢廟相連,就寢的地方,跟宗廟是連在一起的。中國到現在為止,至少在我小時候還是這樣,祖先牌位是擺在家里的堂屋(living room ),初一、十五要祭,不是在家之外另搞一個教堂。所以我說中國人活得很累,活著要為家族盡責任,死了還有責任要保護這個家族,子孫向祖先進供,希望得到保佑。祖先崇拜在中國很突出。中國特別講“孝”,包括大小傳統。漢代皇帝謚號都是“孝”,孝文帝、孝武帝等。有人考證“孝”本是對祖先神的祭祀,后來才轉為對健在的父母的孝順、孝敬。總之,“巫”通由“禮”,性存而體匿,巫術活動的儀典形式不見了,但巫的特征、性格、實質卻長久地保存下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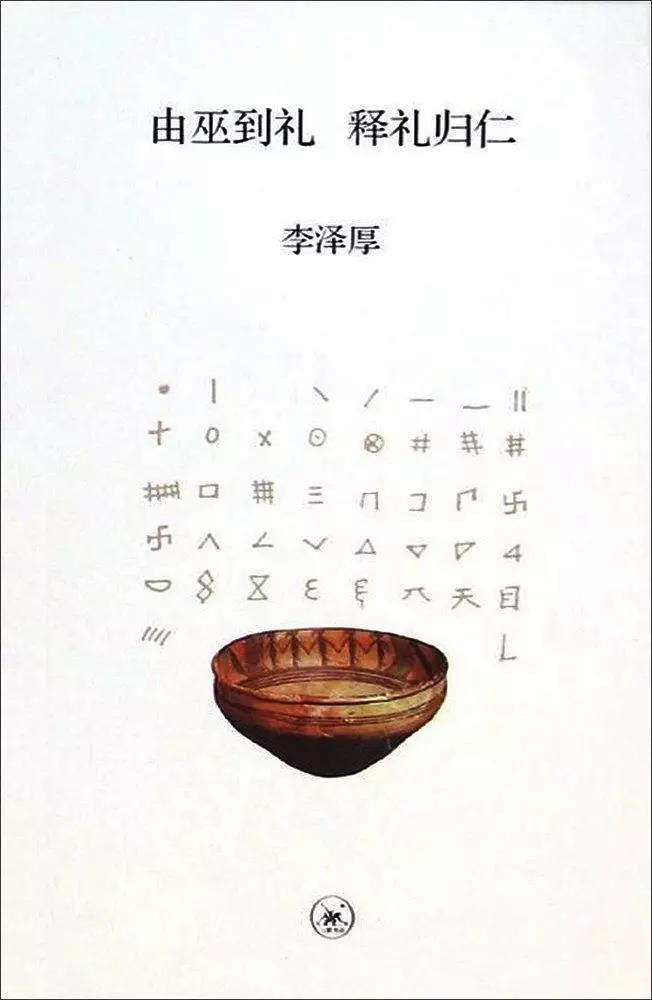
中國禮教是由巫君合一而來的倫理、宗教與政治“三合一”,即中國式的“政教(宗教)合一”。氏族、部族的君、王是首巫,最大的巫,是最高的宗教領袖,也是最大的政治領袖,同時又是氏族德高望重的酋長,集中了政治、宗教、倫理的權能,很早就如此。最近的新石器考古發掘證明,在夏代以前,王權與神權就不可分。玉,是王權的象征。我們看京劇、地方戲,大臣上朝都要拿玉版,這是政治權力的象征。最大的權力象征,當然是王的玉。神仙也有玉。《說文解字》里面有一句話,“以玉祀神者謂之巫”。玉既是巫的符號,也是王的符號,剛才已講了,巫與王相重合。王權與神權,政治權力與宗教權力,是相重合的。有考古學家考證,從龍山時代開始,在夏代以前,王權就明顯大于神權,王是首巫,他的政治權力可以統率群巫。剛才講的巫祝卜史,地位都遠遠在王之下了。又如良渚文化象征王權的“鉞”與象征神權的最大最高的“琮”是放在一個人的墓里。王既掌握了王權又掌握了最高的神權,我以為這是使得中國的巫術直接理性化的一個重要因素。
為什么呢?《左傳》說,“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一個是祭祀,一個是打仗。中國上古時期打仗非常多,部落氏族之間交戰,中國的兵書為什么成書那么早?(《孫子》十三篇,最近有考證表明《孫子》比《老子》《論語》早,是中國最早成書的一部私人著作,這也是何炳棣教授的研究成果。我剛到這兒不久,他寄來一篇文章,還沒有發表。我很贊成他的這個論證。)當然跟中國的打仗經驗有關了,上古時期打了多少仗啊。夏禹時候有萬國,上萬個部落來參加大會,到武王就只剩八百諸侯了,這都是打仗打掉了、被吃掉了,到春秋就更少了,只剩下一百多個,到戰國便只有“七雄”了,打仗,《孫子兵法》一開始就講,必須非常冷靜、理智地去估計各種情形,不能相信鬼神,不能迷信,這是存亡之道,不然國家一下子就滅掉了,這是開不得玩笑的。
《孫子》開篇就強調這個。這是萬千戰爭經驗的總結。我說(何炳棣也贊同)老子源出于孫子,也是“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此君人南面之術也”(《漢書》)。我覺得這個巫君合一、“王是首巫”,王又統率軍隊打仗,對“巫”在中國經由理性化而變為“禮”,起了很大的作用,把巫術這種原來帶有很大的神秘性、通神明的活動,慢慢地越來越加以理性化地運用和解釋,把巫術那套非常煩瑣又神秘的儀式,慢慢地變成了“禮”遠古傳承下來的禁忌、圖騰等以巫術為特色的生活準則、要求,被日益規范化、確定化、系統化:其間當然經歷了一個極其復雜的取舍、增刪、改動、變異的長久演化過程,有許多階段、環節和事件,但這些我們現在很難搞清楚了,只知道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周公“制禮作樂”。
甲骨文有巫字,有舞字,有樂字,但沒有禮字。但孔夫子說,“殷因于夏禮,周因于殷禮”,周代的禮來自殷禮,殷代的禮來自夏禮。所以周公“制禮作樂”,不是周公一個人發明的,而是把前代的禮集大成,使之系統化,全面理性化。這個夏字,清人考證是舞字。或許可以說,夏禮就是原始巫術舞蹈。周公所系統化了的、全面理性化了的周禮,實際上是從夏代或者更早的原始巫術舞蹈開始,一代一代傳承演變下來。到周公那里,把它系統化、理性化了,完成了這個由巫到禮的過程。這是周公很大的貢獻。各種古籍都認為,周公“制禮作樂”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事。宋代以前都是“周、孔”并稱,章學誠有句名言,集大成者是周公,不是孔子。孔子一生也就是學周公,維護周禮。中國人必讀的六本書
關于周禮,現存的典籍有漢代的《禮儀》《周官》和《禮記》,包括政治體制、社會生活、日常舉止許多方面,好些人認為是偽書或后人所作,爭論很大。我一直以為其中保留了從巫術典儀轉化而來的禮制。1980年發表的《孔子再評價》一開頭就講這個“巫術禮儀”的問題,并與當年對少數民族鄂溫克人調查研究相比較,認為周禮是通過“祭神(祖先)”的禮儀擴而成為社會組織、生活秩序的整套規范。其中包括了政治經濟制度、貴族生活規范、社會等級規則,等等。1999年發表的《說巫史傳統》更具體地展開了一些。今天就不詳細講了。前幾年看過美國人伊諾(Robert Eno)一本書The Confucian Creation of Heaven(1990),講孔子是舞蹈大家(the master of dance),儒家的禮是來源于舞蹈,我覺得這跟我的看法比較接近。我一開始就把“巫術禮儀”聯系在一起,認為“禮”是從“巫”演變出來的,也就是把巫術活動的原始舞蹈跟禮樂制度聯系起來。當然,巫術中也有靜默不動的環節,但主要是活動。
禮樂禮樂,樂(原始音樂舞蹈)本在禮(禮儀制度)先,但后來歸屬于禮。所謂禮有幾個特點。第一點,禮者,履也。什么意思呢?禮是實踐,實踐強調的不是人的內心活動,不是個體通神、上天的內心超越,而是個體在現實生活中的行為、舉止、活動,“禮”的許多儀式、規矩、準則、范例,都是針對人的活動、行為、舉止、言語甚至面容而設定的,而且必須有順次、有規則、有秩序地去做,要求得很清楚、很嚴格。《儀禮》所記載的各種禮儀就把人的日常行為舉止規定得很細密、嚴格。有一句話,“無禮則無以措手足”,沒有禮的話,連手腳都不知道怎么擺,禮的實踐性可以到這個程度。禮儀禮儀,禮必須跟儀聯系在一起,禮儀是要人去做而不是要人去想,巫的上天、通神是活動,是去做,而不是去冥思、去想。“禮(禮)者,體(體)也,言得事之體也。”(劉熙《釋名》)合乎禮數的周旋酬對、俯仰往還,無不是通過切身實踐,把方方面面、大大小小的事情做到位,得體、適宜、合度,使人世各種關系在這實踐、操作過程中得到合適的落實。“禮有五經,莫大于祭”,祭禮是最重要的,祭祀把人的各種關系,長幼、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通過儀式的活動即實踐,把遠近親疏上下尊卑安排規范得十分明確。并且以語言、名分確定下來,不能違背,“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老夫子講“為政”,首先便是“必也正名乎”。
所以,禮教又稱“名教”。這就叫“禮別異”,通過“禮”的實踐活動來區分出人在社會生活中不同的位置、責任、義務。到近代仍然是,一個人死了,他的家人要披麻戴孝,但是由于與死者關系的名分不同,披的麻、戴的孝并不一樣,有各種差別,喪服有的要縫邊,有的不縫邊,最親近的人不能縫邊,必須吃最粗糙的飯,穿最劣質的衣服,以表示最大的哀傷,關系遠一些的可以穿得稍好點。各種不同的身份、關系、地位、等級,區分得非常清楚,而且要求不同的情感表現。不像西方,人死了都戴一點黑,動作、姿態、言語、次序等,區別不大。這在中國來說就是非禮。中國的禮講究得很嚴,各種活動誰走在前面,誰走在后面,要求很清楚。磕頭有多種,有的必須碰地,要發出響聲,有的不必如此;有的只叩一個頭就可以,有的要三跪九叩。其實這些都來源于原始的巫術活動,上面已講,很多人類學家研究部族巫術,假如有一步弄錯了,就得處死,因為弄錯一步就認為會給部族帶來災難。中國的禮也類似,非禮是很嚴重的問題。禮是現實生活不可逃避,更不可違背的實踐法規,是不成文的法。
以上是禮的第一個特點,它要求實踐,在實踐中不能違背嚴格的步驟。禮的第二個特點,是對社會生活的全面規范化,不僅僅是祭祀的時候,而是通過祭祀,把整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安排、規定好。中國的家族系統和制度就是以喪禮“五服”等差秩序來制定、規范、推擴出來的,把人的不同實踐活動和這些活動的外在形態包括衣食住行如服飾、食品、住房、步伐等,從而也就把人際世間的現實生活規范、安排成為一個大系統。《儀禮》非常繁細,但被稱為《禮經》,例如,客人來了怎么接待,他坐哪邊,你坐哪邊,他怎么舉酒,你怎么舉酒,都有嚴格規定,不能錯的,錯了就是失禮,是很嚴重的事。
比如結婚,現在很簡單,但是古代有二十四個步驟,問禮呀,納聘哪,規定非常詳細。西方對原始部族的紀錄片里,也可看到很多步驟,但是沒有中國這么復雜。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很多步驟,有很多禮。我這里有一個材料,有七八十項禮的要求,囊括生活的所有方面,吃飯有禮,出門有禮,走路也有禮。到漢代,董仲舒結合陰陽家、道法家把上古這套禮制轉化性創造為“人,天心也”的“有情宇宙觀”,用“天人感應”的“天人合一”方式來作政治制度的安排。殷周以來由巫到禮,行走中的神明變為行走中的天命、天道,到這里就更加系統地政治化了,巫君變為天子,上天、通神變成承擔天命、天道,并接受天譴。
君王(也包括大臣、士大夫)上天、通神的痕跡基本看不到了,但天子必須祭天,而天可以用自然災異來譴責君主(天之子),有地震、天災,皇帝要下罪己詔,要罷免宰相,等等。這個天人感應、天人合一的巫術特征,依然強勁地保留著,對現實生活嚴格規范的禮也依然保留著。從此以后,盡管歷代有許多增刪變異,這基本精神卻一直延續下來。就拿吃飯來說,我記得小的時候,全家一起吃飯,祖母、父親、母親、弟弟和我五個人,必須祖母先拿筷子吃,我們才能吃,自己先動筷子就不禮貌,而且保持一種嚴肅的氣氛,平時也要求“坐有坐相,站有站相”,不許東歪西倒,如此等等。我們已是現代社會的小家庭,都如此,古代大家庭、大家族就更不用說了,非常之講究。中國人吃飯、寫字一般用右手,很少用左手,但在美國用左手的就很多。中國人必讀的六本書
我記得小時候,我妹妹左手用筷子和寫字就不被允許,必須改用右手。《儀禮》鄉飲酒禮,農村老幼在一起宴會,相當于開派對(party),里面有什么規定呢,五十歲的人得站著,六十歲的人就可以坐,六十歲的人吃三個碗,七十歲的人可以吃四個碗,八十歲的人可以吃五個碗,九十歲的人可以吃六個碗。而且在結束的時候,必須老人先走后,年紀輕的才能走。孔子說,“杖者出,斯出矣”。我記得小時候還很注意這一點,年紀大的人先走,我們才能走。這不是政府規定的,也不是法律規定的,而是來源久遠的一種習俗,直到幾千年后都還存在。厲害吧?!
為什么能這樣長久傳承延續呢?為什么這么一套煩瑣的生活規范,卻必須嚴格遵守、履行呢?這就是我要講的第三個,也是最重要的特點:“禮”有神圣性,正因為它非常神圣,所以必須遵守、不可違背。禮來源于巫,巫術里面有神明,因此這些“禮”的規范不簡單,是人間的法規,“禮者,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天經地義,是天地給人規定的。違反了禮,不僅是違反了人間的習俗、規矩、法規,而且更嚴重的是觸犯了神明,那當然就要遭到各種災難、懲罰,民間一直有不孝子孫要遭天打雷劈的說法。所以人的“行”(行為、活動、舉止、言語、面容等)必須符合“禮”的規范,才能與神明、與天地合拍和溝通。所有這些,都恰恰是保留了巫術的基本特征、基本精神,但是把它完全世俗化、理性化了,成了人間的一種神圣的秩序。許多學者講,宗教與世俗的很大區別就是,那個是超乎經驗的世界,這個是經驗的世界。而中國恰恰不是這樣,中國是將這兩個世界合在一起,神就在這個世界也包括在人間的“禮”中,人間的禮儀就是神明的旨意,人與神同在一個世界,所以“禮教”成了中國的“宗教”。
正由于沒有很明確的另一個世界,中國傳統也就很難談什么“超越”,因為沒有另一世界,人又能“超越”到哪里去呢?有詩曰“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問余何事棲碧山,笑而不言心自閑。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中國人喜歡講的是這種回歸自然卻仍然是在這個世界中的心境超脫,而不舍棄身體追求靈魂離開肉體到另一個世界的超越,也就是說,中國人講超脫不講超越。中國人崇拜的“天地國親師”都是相當有現實感的對象,即使是無聲無臭的天意、天命,仍然不是發號施令、全知全能的主宰神。即使神并不全在“禮”中,但仍然缺乏根本不同于人的那種不可認知、不可理解的神。中國講“陰陽不測之謂神”,是說神明在活動中、行走中(這也就是“道可道,非常道”的“道”)的不確定性,而不是一個不可預測不可理解的人格神(personal God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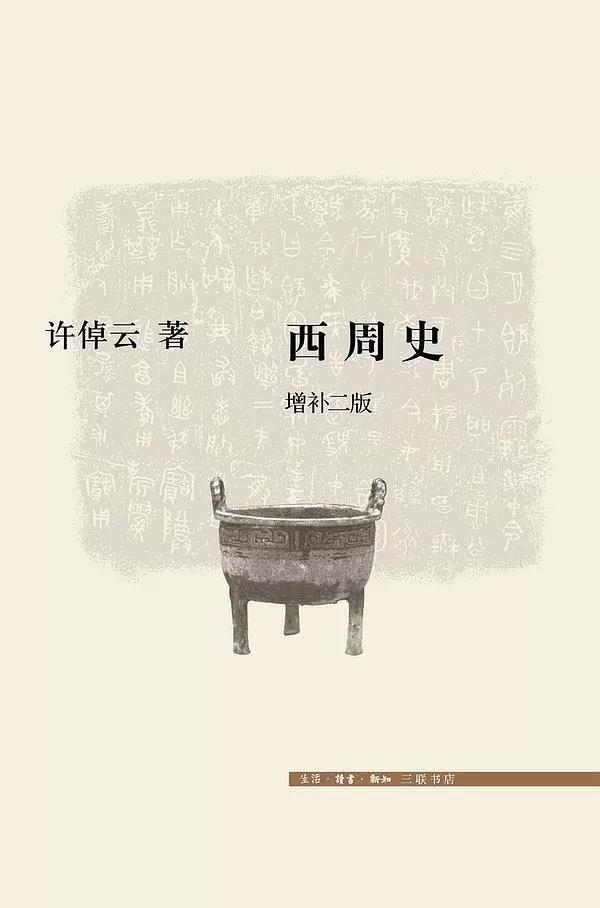
也是在周初,中國講“德”,道德的德。德是什么呢?它最初也是在巫的活動中出現的一種魔力,magic force、magic power,后來變成王的行為、能耐、力量,王是大巫嘛。最后才變成內心的道德。magic force、magic power變成magic moral , magic character,德字里面的心字是后來加上去的,原來所指巫術活動的力量,變成了一種道德、品格,這是一種帶有魔力的心靈:有德的王是圣王,圣(聖)字從耳,因為神明看不見,只能聽到,“圣人之大寶曰位”,上天、通神的圣必須有王的位勢,所以后人把王位看作神器,這都體現出巫君合一的特點。
這些東西都是聯系在一起的。在周初還有一個字,也是比較突出的“敬”字,尊敬的敬。敬的特點是什么呢?現代新儒家徐復觀先生和牟宗三先生有兩段非常哲學化的論述。
徐先生說:“周初所強調的敬的觀念,與宗教的虔敬,近似而不同,宗教的虔敬,是人把自己主體性消解掉,將自己投擲于神的面前而徹底皈依于神的心理狀態。周初所強調的敬,是人的精神,由散漫而集中,并消解自己的官能欲望于自己所負的責任之前,凸顯出自己主體的積極性與理性作用。”
牟先生說:“在敬之中,我們的主體并未投注到上帝那里去,我們所作的不是自我否定,而是自我肯定(Self-affirmation )。仿佛在敬的過程中,天命、天道愈往下貫,我們主體愈得肯定。”
徐先生和牟先生用“敬”來解釋中國哲學的特征。而我恰恰要問這些特征是從哪里來的。我認為是從巫術來的,我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的特點與西方的特點不同,不僅是哲學特點的不同,也包括宗教特點、文化特點的不同,它們來自巫術的理性化,來自巫術沒有被宗教所驅逐,而變成了禮制的精神,即中國的“宗教”(注意:加了引號),即“禮教”“名教”。中國的特點是,天大,人也不小。《老子》里講,“天大地大王亦大”。西方不是這樣,上帝極大,人很渺小。中國的“敬”不是寄托在崇拜對象上,一切依靠上帝,而是放大自己的主體力量,通過自己的活動使神明出來。為什么?哪里來的?巫術里來的。
與許多民族從巫術走向宗教不同,中國從“巫”走向了“禮”,巫術中那些模糊、多元、不確定卻在行走中的神明變成了“禮”在履踐中的神圣性,它的內心狀態變成了那同樣是模糊、多元、不確定卻在行走中的“天道”“天命”出現在自己(個體)行為活動中的神圣感、使命感、責任感,也就是兩位先生講的“主體”“自我肯定”的“積極性”。這就正是我講的巫的理性化。
中國的“禮教”與基督教等不同,它可以允許人們去信別的宗教的神、拜別的菩薩。為什么?因為那些神、那些宗教只關乎個人的生死、身心、利害,而不是“天道”“天命”關系著整個群體(國家、民族),這恰恰是原始巫術活動的要點:是為了群體生存而非個體命運。這也就是中國缺乏個人主義的原始根由。
盡管巫醫相連,巫也治病、養生而關乎個人,但作為“巫君合一”的大巫演變為君王以后,便主要是主政,作為政治、軍事首領來承擔天命、治理百姓而非著重個體了。由巫到禮之后,更是如此。這是政治方面。在社會方面,由禮教所構建形成了“中國生活方式”(重現世生活、人倫關系、情感價值,并把它們提升為神圣性的信仰),并以此既抵制又容納和同化了許多不同的族群、文化和宗教。這從兩漢、魏晉到隋唐一直延續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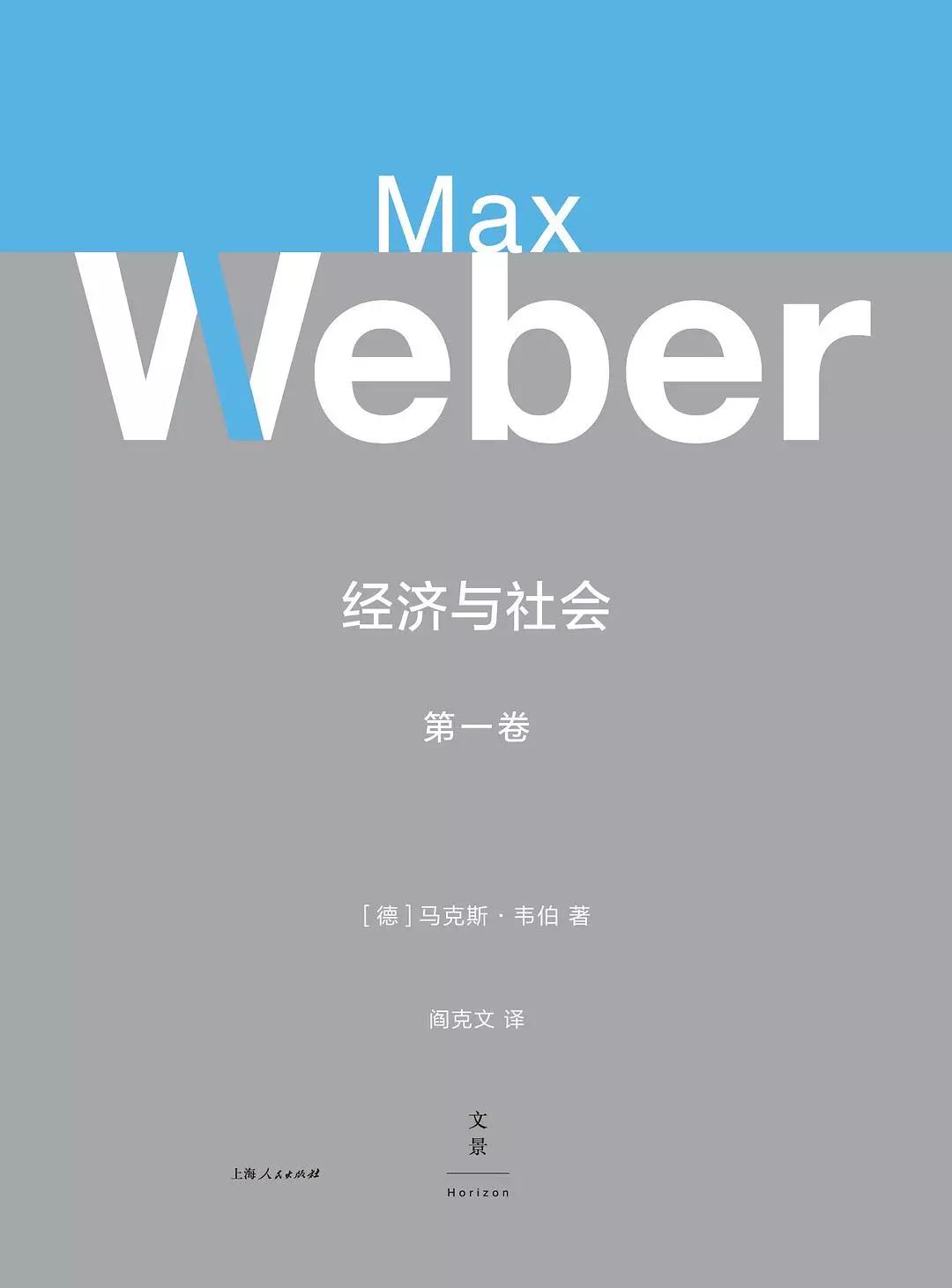
從內在心理方面說,“德”“敬”作為主觀心理狀態都與“巫”有關,是由“巫”演變即理性化之后的產物。它們把巫術中有關“愛”的迷狂情感和神秘魔力理性化了,成了世俗化和人際化的道德、品格、心理。所謂“理性化”也就是將理知、認識、想象、了解等各種理性因素滲入、融合在原始迷狂情緒之中,并控制、主宰這種迷狂,成為對人們(首先是首領、巫君)的行為、心理、品格的要求和規范,這也就是上面已強調過的巫的情感特征的轉化性創造。但是,“鬼神乃二氣之良能”“思之思之,鬼神通之”,特別是宋明理學受佛教影響,大講半日靜坐、孔顏樂處等等之后,便又把這種巫術通神、上天的神秘經驗在后世傳承甚至更加張揚出來,甚至到今天。在哲學上,牟宗三講“智的直覺”,馮契講“轉識成智”,都可看作是它的展現,即以超出或超越理性的方式去獲得真理、感受生命、“體知”天意(或天命、天道)。
孔子有“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的自命,孟子有“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的自信,但我以為,這里重要的恰恰是將原始巫術的上天、通神的特色,轉化性地創造為對世間人際的一種飽含情感而又理性的歷史使命感與社會責任感,即對所謂天命、天道、天理、天意的承擔。正如巫的上天、通神本身并非目的,而是為了求雨、救災一樣,儒家的“內圣”也并非目的本身,而是為了“外王”。孔子所說高于“仁”的“圣”,是“博施于民而能濟眾”。巫的上天、通神的個體能耐已變為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的個體情理結構,巫師的神秘已變為“禮—仁”的神圣。這神圣不在所崇拜的對象,而就在自己現實生活的行為活動、情理結構中,這才是要點所在。文天祥說:“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岳,上則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為嚴將軍頭,為嵇侍中血。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
巫史傳統承續下來的,就是這種理性化而又飽含情感的情理結構:一方面是超脫世俗、回歸自然,上下與天地同流,另一方面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知其不可而為之。總而言之,周公“制禮作樂”是對原始巫術的外在理性化,孔子“歸禮于仁”則是承繼周初的“敬”“德”而將之內在理性化了。這也就是“由巫到禮”“由禮歸仁”,即巫的內外理性化的中國傳統。
記得幾年前在一次對談中,我說史華茲(Benjamin Schwartz)喜示中西之同,葛瑞漢(A. C. Graham)好揭中西之異,我傾向于后者,因我覺得明其異才更識其同。我強調巫的理性化,一直不贊同說中國早已政教分離,古代巫術已進化到宗教,巫已消失,也不贊成韋伯(Max Weber)的脫魅理性化必須在近代,也不接受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的軸心突破說。我強調認為,巫進入禮,以后釋禮歸仁,其基本性格(情感性、活動性和人的主動性)仍然存在,即所謂“性存體匿”。西方神學正統不講人與上帝合一,只有人去皈依上帝,上帝全知全能,甚至不可認知而只能信仰。中國則是,天也要講道理,天也得聽老百姓的,“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甚至人可廢天,“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等等。因為,天道即人道,而且天道來自人道。由此也可見中國是一個世界,西方是兩個世界,所以只有中國才有“天人合一”,而不同于西方的“神人異質”,不同于希臘與希伯來的理式與現實、天堂與俗世、靈魂與肉體的截然兩分,前者為本源、真理和道路,后者只是模仿、墮落和罪惡。中國巫史傳統沒有這種兩分觀念,才可能發展出實用理性和樂感文化,它追求中庸與度,講求禮仁并舉、陰陽一體、儒法互用、儒道互補、情理和諧,顯然不同于西方傳統的上帝至上、理性至上。
“由巫到禮”的理性化,當然不止于儒家,我在《美的歷程·先秦理性精神》和《說巫史傳統》里都突出提到和論列了道家及各種思維范疇,今天就不詳細講了。大家如有興趣,可以去翻翻那些文章。
我一開頭說,“由巫到禮”是一個比較難講的題目,而它的重要性被忽略掉了。因為研究得很不夠,我只能就其重要性即對中國文化、中國哲學的源頭性的特征這一點提示一下。最后我想用幾段過去的話來作結尾。
“周禮是什么?一般公認,它是在周初確定的一整套典章、制度、規矩、儀節。本文認為,它的一個基本特征,是原始巫術禮儀基礎上的晚期氏族統治體系的規范化和系統化。作為早期宗法制的殷周體制,仍然包裹在氏族血緣的層層衣裝之中,它的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直接從原始文化延續而來。”(《孔子再評價》1980)
“禮儀即人文,它本是任何遠古民族都具有的神圣制度,通由它團結人群,鞏固秩序,建立人性。它最早是巫術:一種象征性的精神生產,亦人類最早的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以此,人類行為的整個領域,皆被納入巫術性象征主義羅網中’,‘即使最輕微的背離……都將導致整個儀式無效’,‘美洲印第安巫師在主持宗教舞蹈形式時,唱錯曲子的人立即處死,以免神靈生氣’(韋伯《經濟與社會》第二部)。在中國,如何由遠古這種巫術儀式逐漸演化推進為殷商禮制,即如何逐漸理性化和政治化(在中國,這兩者是同一過程),宗教性與政治性如何組織結構,乃上古思想史尚未解決的重要課題。中國人必讀的六本書
如前所說,我以為,中國巫史文化使原始巫術與倫理政治融同,形成‘三合一’的禮制,它是倫理,又是政治,又是宗教。正是此種‘三合一’,才形成了以情為本體的儒學和隨后的‘儒道互補’‘儒法互用’。‘道’‘法’為形式,‘儒’仍為心魂,其緣由正在于它由巫術型的文化傳統而來,成為中國上古的‘巫史文化’。巫的特征之一是人能主動地作用于神,重活動、操作,由此種種復雜的活動、操作,而與神交通,驅使神靈為自己服務,這與僅將神作乞求恩賜的祈禱對象,人完全處在被動祈禱的靜觀地位頗為不同。各原始民族都有巫術,今日現代生活中也仍有巫的痕跡。但中國巫術傳統因與政治體制和祖先崇拜相交融混合,并向后者過渡而迅速理性化,就形成了一種獨特傳統:巫(宗教領袖)也就是王(政治領袖),禹、湯、文王都是大巫師,死后更成為崇拜對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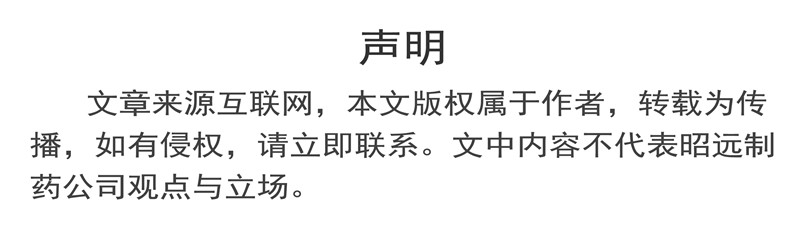
- 上一篇:梁漱溟:思維的八個層次,你在哪一層?
- 下一篇:王鼎鈞:很多故事,我們只知道半截




